点击查看:传教士与圣谕广训.doc
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 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 司 [摘 要] 佳 文章围绕笔者曾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档案发现的十多种有关清代《圣谕 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从历史学与语言学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并结合当时其他传教士所作的多种 翻译、评论史料,探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入门材料这一“传统” 之源起。文章进一步剖析传教士关注《圣谕广训》与《广训衍》及《直解》的不同出发点,即从 《圣谕广训》的翻译文本中获取根本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借鉴《广训衍》、《直解》之类的浅 文理形式作为习得汉语的捷径。作为初入异文化空间的新教传教士,面对“他者”的文化根基,其 早期的学习态度与相应之传教策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圣谕广训 传教士 卫三畏 方言直解 [作者简介] 司佳,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美国汉学 清代的《圣谕广训》因在各省以方言、白话定期宣讲的关系,直至清末于中国地方民间都有 着不一般的影响力。周振鹤先生在《<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一书有关“《圣谕广训》的汉语方言 本”一章中讲到,因为汉语方言很难用文字书写来表达,所以讲解《圣谕广训》的方言稿本不会很 多,多可能是请对地方方言娴熟的知识分子来编写《圣谕广训》的方言讲解稿。周先生研究过复旦 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本吴语《圣谕广训直解》,另提到一种用浙江嘉兴方言写成的《圣谕广训通俗 》,并述及除此之外,方言本(包括手抄本)《广训》的材料所见不多。1 然而,十九世纪新教传 教士因为布道交流与口语学习的需要,往往会注重收集这一类官话与方言、土白两相对应的语汇材 料。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卫三畏家族档案(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中,笔者 便有幸发现多种有关《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件。 除了周振鹤先生的著作以及此前日本学者鱼返善雄所编《汉文华语康熙皇帝圣谕广训》之 * 1 本文的研究为复旦大学章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 转型”(编号 09&ZD07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于 2012 年 4 月 15 日由上海史学会主办的“首届 上海史学会青年论坛”上宣读,得到熊月之、陶飞亚等教授的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615-617。 1 外,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先生于 1985 年亦撰文讨论《圣谕广训》及《广训衍》对清 代地方白话及俗文学发展的影响。2 此外,台湾的王尔敏先生还专门对《圣谕广训》与清代民间宣 讲拾遗的风气进行研究,并指出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布道宣教时参考借鉴了民间宣讲圣谕这一形 式。3 而近年来在有关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开始关注十九世纪初来华新 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人翻译、学习清代《圣谕广训》及《圣谕广训衍》的原因。日本学者内田 庆市指出,新教传教士学习《圣谕广训》,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成为传教士内部学习汉语的一种 “传统”。也有学者认为,传教士以之为主要学习文本,与其中的道德教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或 为与宣讲形式存在更多关联。4 本文在梳理前人尚未充分关注的卫三畏家族档案第 13 箱中有关清 代《圣谕广训》多种方言手抄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选取《圣谕广训》及 《广训衍》作为汉语学习的“敲门砖”的根本原因。 一、卫三畏家族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十三种 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档案(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对于研究美国最早来 华新教传教士之一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的生平经历有着特别的史料价值。5 1833 年,卫三畏由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任至 广州,作为印刷工参与新教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传教工作。1834 年,他开始协助裨治文(E. C. Bridgman)编写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并成为鸦片战争之前英美传教团体在广州的 主要执笔人。1853、54 年他曾两次担任翻译参加美国黑船舰队开赴日本的行动,初展外交及语言 才能。1856 年起,卫三畏离开美部会,以外交官的身份长期居住于中国内地近二十年,直至 1876 年离开北京返回美国。期间,他曾参加过 1858 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促成双方在条约 中加入了允许在通商口岸城市传播基督教这一关键性条款。 6 卫三畏的主要著作有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1848 年初版及 1883 年修订版),以及语言工具书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拾级大成》1842),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英华分韵撮要》1856),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英韵府》1874)等。由于卫三畏 1877 年返美后不 久便接受了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席位,同时也是开创美国汉学之第一人,加上家族三代中 2 Victor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in David Johnson et al.,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 3 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收入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 究》,页 633-649。 4 这个问题曾在 2010 年 10 月 30-31 日召开于日本関西大学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引发部分 学者的热议。 5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MS547),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6 关于卫三畏生平经历的研究,主要参考 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8),中译本《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均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以及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研社,2009 年)。 2 不少成员都跟耶鲁大学有关,因而其家族档案不仅内容丰富,且得到后人对保存工作的极度重视。 根据耶鲁大学图书馆所编的档案目录索引,第 1 至 18 箱主要涉及卫三畏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相关 资料,包括书信、剪报、照片、著作手稿等。第 19 至 24 箱为卫斐列(Frederick Williams)的手稿 资料,卫斐列为父亲卫三畏撰写了生平传记,后亦任教于耶鲁大学。档案其余部分则是卫三畏 1877 年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首任教授后开设课程的讲义资料,亦由卫斐列整理。笔者曾于 2002 年、2007 年以及 2011 年三次访阅该档案,对第 11 至 17 箱手稿中所涉及的中、英文语汇资料 进行整理研究。7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卫三畏个人的了解主要依赖其子卫斐列(Frederick Williams)撰写的传记 。这位东方经历颇为丰富的美国人,一生兼以印刷工、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等数职,在中国度 过了四十多年。如果说一本百余页的传记乃是反映卫三畏一生东西方迂回历程的点睛之作,那么至 今于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保存完好的三十余箱家族档案则可投射出卫三畏日常生活的色彩斑斓。 档案中所藏卫三畏早年到达广州后与家族、亲友的通信,以及部分时段的日记、报章评论,对了解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关系有着一手的史料研究价值。档案中另藏有多种卫三畏在中国 南部沿海学习官话、方言的笔记资料,以及其编著中英字典及汉语工具书的相关笔记、手稿等,对 全面了解十九世纪初中英语言、文化接触的详细过程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传教士充任“业余 汉学家”的十九世纪,由于缺乏完备的中文教学条件,系统地收集、整理中文语汇即成为编写汉语 工具书的重要一步。编者们往往会在整体而系统的收集、整理之后才决定取舍,而手稿正是可以看 出其中“取”与“舍”的关键。 在档案第 13 箱中,语料价值最高、收藏最为系统的当属与清代《圣谕广训》有关的十余种方 言直解及罗马字注音抄件。在编号为 130052 的文件夹中,存有 13 种与清代《圣谕广训》有关的抄 件,涉及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吴方言及闽方言。这些抄件被列入 Miscellany(杂项)条目之下,没 有内容标题。正因为如此,之前甚少有人关注到此乃研究清代《圣谕广训》及《广训衍》极佳的方 言手抄资料。略为可惜的是,这些抄件仅仅是对《圣谕广训》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的方言释 义,没有涵盖到全部的十六条。原因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一般会选取中国地方文学样式作为研究、学 习的“样本”,仅以《圣谕广训》第一条作为学习的范例,并无大碍。然而,卫三畏不仅请他的中 国“先生”仔细抄录了此第一条,还逐字逐句对照方言字汇,并加以罗马字注音;其中有若干种直 接用地方方言写成,当属《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因后世留存的方言本《圣谕广训》并不多 见,卫三畏家族档案中所藏的方言直解虽然只是片断(仅第一条)抄件,仍然具备相当高的历史语 料价值。现将笔者经眼的卫三畏家族文书中有关《圣谕广训》的 13 种抄件之名目以及大体的书写 样式、特点、使用字词语汇(方言、官话)等汇总如下: 7 在最近的一次重访中,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部的帮助,允许将相关材料电子复制。 3 第1种 标题 版式 材料基本描述 方言词句摘引 8 Ningpo Colloquial 共 3 页,竖 用宁波地方话写成的方言直 弗晓得、也弗忖忖; 排从左至右 解,然仅关涉雍正《圣谕广 若是笑兑大人就欢喜;到 书写 训》第一条“敦孝悌以重人 拉成人长大又替其娶一房 伦”中的内容,并在每一个 家小;大人个恩惠实在像 汉字右边加以罗马字注音。 天介大。 详见附录 第2种 Sound of Characters 共 2 页,自 为雍正《圣谕广训》第一条 as Read at Ningpo 左向右竖书 “敦孝悌以重人伦”的逐字 注音,宁波方音土白。 第3种 Su-chow Colloquial 共 3 页,自 用苏州话写成的方言直解, 弗晓得、也弗想想;若是 左向右竖书 亦仅涉雍正《圣谕广训》第 笑末大人就欢喜;伊后来 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中 长大成人又替伊攀一家 的内容,并以罗马字注音。 亲;爷娘个恩惠同天能个 大。 第4种 Sound of Characters 共 3 页,自 对雍正《圣谕广训》第一条 as Read at Su-chow 左向右竖书 “敦孝悌以重人伦”加以逐 字苏州话注音。 第5种 第6种 Rendered into 共 2 页,自 用福州话写成的方言直解, 卖晓得、都不想;至成人 Foochow Colloquial 右向左竖书 仅涉《圣谕广训》第一条, 长大仅着替伊讨亲;罢奶 并以罗马字注音。 其德实在比天故大。 The Sounds of the 共 2 页,自 对《圣谕广训》第一条加以 Characters All 右向左竖书 福州话逐字注音。 Extract from 共 2 页,自 抄自雍正《圣谕广训》第一 Paraphrase of the 左向右竖书 条“敦孝悌以重人伦”,每 Given as Read in the Foochow Dialect 第7种 First Maxim in the 个字的右方以罗马字注音。 Shing Yu 第8种 8 无标题, 自左向右竖 乃对雍正《圣谕广训》第一 不晓、做年、不、想着; 书,正反面 条“敦孝悌以重人伦”的逐 欢喜、就、兑子、欢喜; 此栏摘录的方言词句所对应的雍正《圣谕广训》中的原官话词句逐次为:不知、独不思;笑则为之喜;至于成人 复为授家室;父母之德实同昊天。 4 共9葉 第9种 第 10 种 第 11 种 无标题 无标题 无标题 字吴方言释义,并在每个字 爹娘、個、功劳、真亲像 的下方注以罗马字读音。 、大、天。 自右向左竖 也是对雍正《圣谕广训》第 唔识、单唔想、介伊、欢 书,竖分 3 一条的逐字方言释义,并在 喜;及到、人子完全、再 栏,共 7 页 每个字的右边加以罗马字注 格共伊娶妻;爹娘、個功 音。 、真、亲像、青天。 自左向右竖 将雍正《圣谕广训》(第一 勿晓得、啥勿想;笑末就 书,共 4 页 条)与清后期的一种吴方言 为之伊快活;直到成功大 直解本逐字比对,并对吴方 人替伊讨娘子;爷娘个好 言直解加以罗马字注音。 处实在像天能。 自右向左竖 乃一种用地方土白写成的《 勿晓得、啥勿想到;笑之 书,共 2 页 圣谕广训》吴方言直解,有 末就快活;直到大要讨娘 句读,无罗马字注音。从方 子拉伊;爷娘个恩典大来 言字词的使用来看,很可能 像天能。 是用于上述第 10 种比对稿 的吴方言直解底本。 第 12 种 无标题 自左向右竖 汉字部分为雍正《圣谕广训 书,一页两 》第一条,而每个字右边的 栏,共 8 页 罗马字注音却是基于某种吴 方言的拼读。与上面第 10 种相比,省却了中间的吴语 直解汉字部分,末有 S. W. Williams 签名。 第 13 种 无标题 自右向左竖 是一种用吴语写成的方言直 不晓得、不是单把……没 书,共 3 页 解,仅涉《圣谕广训》第一 有想吗;或是笑就喜欢; 条中的内容,逐字配以罗马 到了成人还要替他配亲; 字注音,书写笔迹与前面提 爹娘的恩点实在是像天一 及的 11 种有明显不同,可 样没有极处。 能是出自十九世纪中期在东 南沿海活动的其他美部会传 教士之手(似裨治文笔迹) ,收入卫三畏的档案中。 5 卫三畏家族档案中所见上述 13 种与清代《圣谕广训》有关的抄件皆与中国沿海方言有关,其 中 6 种可以确定分别是苏州话、宁波话及福州话(注音与直解各一种),因卫三畏在这 6 种材料上 分别注明了 Su-chow, Ningpo 与 Foochow 的字样。其余则主要涉及吴方言,有 5 种之多(不计已经 注明的苏州话与宁波话材料)。所有抄件除最后一种之外,皆附有罗马字注音,可见传教士在汉语 学习过程中对方言注音这一传统的重视。从手抄的体例以及罗马字注音的笔迹来判断,这些手稿很 可能是卫三畏与他的中国先生们的共同作品:汉字以工整的小楷竖向抄写,一旁或下方注有罗马字 拼音,这也反映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学习汉语时“字音并重”的特点。 另外一大特点则是官话与方言、土白并重。上述第 8、第 9、第 10 三种皆以《圣谕广训》的 官话表达与方言释义(或直解)两相对照,显示出这些手稿抄件作为学习中国沿海方言的特殊用途 。第 11 种更是在官话的一旁用方言字词的读音直接标出,凸显出这其中方言方音学习的重要性以 及技巧,即一种对照文言读出方音的记忆方式(因方言字词的书写只是一个中介,对于传教士来说 ,最终的习得目的是用方言或土白与当地人进行听说交流)。《圣谕广训》、《广训衍》以及《圣 谕广训直解》显然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非常关注的中国文学样式。稍有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卫 三畏收集这些与《圣谕广训》相关的方言直解仅是为了今后著书之用,上述 13 种资料皆止限于《 圣谕》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不过,这并不影响早期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时侧重 对语言“样本” (specimen)的积累。在卫三畏 1842 年完成的第一部汉语学习工具书《拾级大成》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中,有关《圣谕》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的白话文衍义(清王又朴 作)即作为“浅文理” 的文学样式列出(原文称作 paraphrase of a Maxim),与《红楼梦》(选 段)、《三字经》等一并置于汉语学习拾级(全书共分十章)中的“第九级”(the ninth step), 皆以罗马字注音并逐字对译,为传教士习得汉语“浅文理”提供有用的样本材料。 诸种文学经典的浅文理“样本”也给十九世纪的传教士们描写各自笔下的“中国”提供了详实 有据的材料。在卫三畏 1847 年完成的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1848 年初版,1885 年 修订版)一书的序言中,作者批评了当时“游历中国的旅行家”因为缺乏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深入了 解而轻易下笔,导致诸多文明现象被讽刺、歪曲。“因此,我的意图是,通过对他们的政府及其行 为准则、文学和科举考试的梗概以及社会、宗教状况,进行不加雕琢的描述,就像讲述其它国家一 样,将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这将有助于修正或补充这些观点于万一”,卫三畏进一步阐明,“这 一著作中,几乎每一部分的资料来源,都是亲自观察和对当地权威性典籍的研究”。9 与之相应, 在述及清代皇帝 “政治讲道”这一问题时,卫三畏专辟章节对《圣谕广训》的文本性质、宣讲形 式等条分缕析:“由统治者印发的诸多训导百姓的文件中,最具影响的无过于《圣谕广训》,由米 9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7), Preface xv -xvi; 中译本卫三畏著《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页 2-3。 6 怜博士翻译了这篇政治道德论文,而为英国所知”;“为了使《圣谕广训》做到家喻户晓,不许漏 掉一人不知,制定法律要求全国地方官员于每月初一、十五在公众场合进行宣读,……虽然设想可 嘉,但实际上除了大城镇之外并未得到重视”。 10 在将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逐一译成英文 并对雍正时期的《广训》作了基本引介之后,卫三畏还专门引用了米怜翻译的原由王又朴所作《圣 谕广训衍》中的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引文原文为米怜翻译的英文,这里因为是中文表述的 关系,故直接引用王又朴的原作): ……尤其可怪者,天上至尊莫如玉皇大帝,若确有如是明神,为何不在天上安享居 乐,而需待尔为之塑金身,造屋以处之?斋戒、集会、造庙、塑像,种种无谓故事,皆 由逍遥无事之和尚僧人所捏造以欺尔等者也。11 卫三畏特别选取了圣谕十六条中集中论述民众信仰的文字,很可能有一番用意。出于争取信众 的心理,十九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地方信仰尤其关心,有传教士还专门 访问寺庙,观察记录老百姓的膜拜方式。《圣谕广训》本身也带有强烈的伦理教化意味,每一条都 能够透视出官方如何引导民众的道德、信仰取向,因而成为传教士获取中国本土百姓“内心信仰” 的信息来源。卫三畏最后提到了《圣谕广训》另有一些方言土白本,为教授孩童所用,并自己尝试 用英语的诗歌形式翻译了其中的第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12 《中国总论》此处的英文原文虽然 没有注明翻译所依据的底本,也未曾附上明确的土白本原件——不过翻阅有关藏目之后,可以推测 卫三畏此处的翻译正是基于其个人档案第 13 箱中的相关“收集”,即上文所述与清代《圣谕广训 》有关的方言直解及罗马字注音抄件。 二、传教士研习《圣谕广训》及《广训衍》之缘由 在阅读基本档案之余,笔者深感这些语料价值极高的方言罗马字注音材料也可以给“传教士缘 何学习《圣谕广训》”这一问题提供研究线索。《圣谕广训》是中国老百姓天天需要学习的,因而 十九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在内地各省不仅可以得到像《圣谕广训衍》或《圣谕广训直解》这样的官 话土白本,也不难接触到跟《圣谕广训》有关的方言直解本,尤其是在沿海主要方言区域。自十九 10 《中国总论》中译本,页 477。译者原文为“由美魏茶博士翻译”,有误。美魏茶是 Williams Charles Milne 的中 文译名,乃米怜(William Milne)之子。另,第十二章 “中国的雅文学”的英文原文为 Polite Literature of Chinese,译文也有细微出入。 11 《中国总论》中译本,页 477-480。 12 卫三畏的翻译共有十个段落,皆有韵,以诗歌形式体现原方言土白本中语词生动之处,读来琅琅上口。此处例举 第一小段: “The parents’ tender care can be dispensed, Not till three anxious years their child they’ve nursed; A father’s watchful toil, a mother’s love – E’en with high Heaven equality demand.” 7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于中国南部沿海活动势力一路北上,跟通商口岸相关的广东话、厦门话、福州 话、宁波话、上海话及周围的其它吴方言材料,多编入传教士所作的词汇手册。卫三畏在 1842 年 出版的《拾级大成》中使用过《圣谕广训衍》作为学习中文白话的材料,之后卫氏因职而北上—— 汇集此多种《圣谕广训》方言直解,也可能跟进一步编写语言工具书的计划有关,这也可以从卫三 畏对这些材料逐字注音、释义等细节看出。更多有关《圣谕广训》的介绍与评论则出现在卫三畏的 代表作《中国总论》中,用以管窥清代官方如何将皇帝的旨意教化于民。正如他在 1847 年撰写的 初版序言中所说,“作为在广州和澳门居住过十二年的人,每天和人们亲密来往,说他们的语言, 读他们的书,可以设想,这就使我有可能解说他们的政体和特点的一些部分,而这在美国还不为人 们所普遍了解”。卫三畏并非关注《圣谕广训》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然而就他本人手稿中的“收 集”方式来看,显然非常认同《圣谕广训》的语料价值,尤其是它在各地方言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多 样性。 窃以为,探究新教传教士为何以《圣谕广训》作为学习汉语的基本阅读材料,还可以进一步从 文本的语言特点及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传教士学习跟《圣谕广训》有关的衍说、直解一类 文本,当然与熟悉中国地方土白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十九世纪初可以给新教传教士提供“浅文 理”的材料还有很多,比如《好逑传》、《西厢记》、《红楼梦》这一类戏曲、小说、传奇等文学 样式也是传教士习得中文白话的主要范本。因而,传教士对《圣谕广训》及《广训衍》这类文本进 行翻译、介绍之兴趣根源,或许跟基督教伦理教化的因素有着更多的关联。比如,在早期来华新教 传教士马礼逊等人看来,清代《圣谕广训》在民间以口语形式宣讲,不仅在文字传教方面给传教士 以一定启发,其宣讲仪式本身也可以为新教在地方上的“直接布道”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参照。13 而 作为严谨的基督教徒,传教士们在看待《圣谕广训》及《广训衍》此类文本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着 眼点便是需要凭藉一个权威的中文文本,将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范畴与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体系 加以比较、区分。 伦敦会早期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于 1815 年底在马六甲完成了第一种 英文全译本(系以清代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为底本),1817 年在伦敦出版。在序言中,米怜 首先介绍了从康熙《圣谕》十六条至雍正《圣谕广训》、再至王又朴编写《圣谕广训衍》的书写发 展脉络,并将这三种文本的语言特点、宣讲方式、使用对象等略加比较。显然,王又朴的作品因富 含方言俗语,明白如话,以应宣讲圣谕为地方百姓理解之需,得到了米怜的褒许。米怜接着讲到了 道德、法令的宣讲于中国古代《周礼》所记之源头,并大致介绍了清代宣讲圣谕的仪式和过程。然 而,站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立场上,米怜将《圣谕广训》中所示的道德教化内容作为“异教国 家”没有经过所谓“神启”的自然萌发状态,与自身基督教文化中经过“神启”的、有系统性的道 德准则加以区分。他指出,作为《圣谕广训》的英译本读者,即便是笃信上帝为一切道德信条之源 13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pp. 89-90. 8 泉的基督徒,也不必担心这一来自异教国家的文本会对他们的福音信念构成威胁。原因在于,虽然 《圣谕广训》体现了一种中国人自发的道德观念,“但其中却不包含关于上帝、灵魂及永生等终极 关怀”。14 因而,米怜认为,虽然新教传教士第一次面对道德范畴如此复杂的中国文化,也大可不 必将之与基督教观念全然对立或相互消解;而是应当以基督教的福音对此向善的观念进行增强。 为了纪念米怜的这项工作,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的编者于 1847 年第十期转载 了英译本的部分内容,并对雍正《圣谕广训》及王又朴所作的《圣谕广训衍》作了详细介绍。文章 首先对《圣谕广训》的作品性质进行阐释:“此书论及(个人的)道德责任以及(国家的)政治经 济;与类似的中文作品一样,以‘孝’先行,然后谈及由‘孝’衍伸出来的其他相关伦理准则及其 要义”。15 文章进一步评论了《圣谕广训》的写作理路,并指出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基性。 不过,这种在当时中国人看来乃最自然不过的父母—子女之关系,在传教士眼中却成为“异教国 家”为“最荒谬的偶像/祖先崇拜”所寻取的文本上的支持而已。 从传教士的一系列相关评论来看,对《圣谕》、《圣谕广训》及《广训衍》(或《直解》等白 话、衍说)三种不同文本的关注另有其它的考虑。《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乃用文言写成, 对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学习中国地方土白基本上没有直接影响。因而传教士大多探讨的是其 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时或将之与基督教的伦理教义联系比较,得出的结论多是皇帝的言辞并不能 给予中国百姓来世的关怀。而传教士对《广训衍》的关注则更多偏重于语言、文体方面的考虑。上 文提及《中国丛报》的编者便对《圣谕广训》与《广训衍》两者的文体结构进行过比较,认为《广 训》虽以雅言书写,在谋篇布局上却略有斧凿之嫌,时有赘冗之处。而《广训衍》则可以面向更广 泛的读者群,其谚语俗语、方言土白不仅能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理解,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也可提供 有效帮助。虽然有时白话体中出现的虚词、连接词对于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有一定难度,但是跟《 广训》本身相比,《广训衍》相对较易理解,应当先习得这种“浅文理”,有助于进一步的文言文 学习。另外,执笔者还指出,《广训衍》的这种写作方式或许可以成为传教士向中国百姓口头布道 的范本,甚至可将之奉为新教传教士中文布道手册编写的文体范例。16 同样,传教士对《圣谕广训直解》的翻译也是主要为了学习白话及地方口语。《圣谕广训直解 》是另一种《圣谕广训》的白话讲解本,于清同治年间起逐渐流传于全国各地,比之于王又朴的 《圣谕广训衍》,其解读更为直白明了,主张愚忠、愚孝的口吻也更似直接。17《圣谕广训直解》 的英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于 1892 年翻译完成的,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鲍 氏以《圣谕广训直解》的白话部分为底本进行翻译,在扉页中注明是为了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新来的传教士准备的语言学习材料,并另配一册 Vocabulary of Sacred Edict(《圣谕词汇 14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t,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London, 1817),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xi-xv. 1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Oct. 1847), pp. 500-506. 1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Oct. 1847), p. 503. 17 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607。 9 集》),按部首分类排序,以供初学者之便。在鲍氏的翻译中有逐条的圣谕以及相应的直解,却没 有涉及《广训》。在序言中,鲍康宁直言口语学习对于传教布道尤其重要,《圣谕广训直解》富含 日用口语、俗语及民谚,能够传达中国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鲍康宁也提到中国的小说及佛事文书 也可以为学习白话、俗语提供材料,不过学习跟《圣谕》相关的内容,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百姓的 日常生活特点以及他们的道德伦理规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跟《圣谕》相关的文本作为汉语学习的资料也被纳入到天主教传教士 编选的中文—拉丁文对照学习课程中。在耶稣会士 Angelo Zottoli(晁德莅)编写的五卷本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国文化教程》)中,《圣谕广训衍》全本十六条位列首卷首篇。编者晁德 莅神父于教程的序言中指出,在这套设计为五年课程的教材中,初级班也就是第一年的学习,侧重 的是日常用语,包括日常习语、戏曲中的对白、传奇故事、才子佳人小说等,《圣谕广训衍》即列 为首选。之后在第二年的课程中,学生才开始熟悉小学(《三字经》、《千字文》等)以及《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进而第三年逐渐过渡到《五经》的研习,第四年专攻 虚词、书函写作及文学典故等。最后一年则加强修辞方面的训练以及学习写作对联、诗赋等。18 根 据邹振环先生的研究,晁德莅 1848 年来华,1852—1874 间年担任圣依纳爵公学(Le College St. Ignace)校长,期间完成了这套拉丁文—中文巨著,于 1879—1883 年出版《中国文化教程》。 19 而笔者所见的这套《中国文化教程》,其第一卷则于 1909 年由上海土山湾出版,第二卷却于 1879 年出版。卷二也有一篇序,不过仅针对第二卷的内容,与全套的谋篇布局无关。晁德莅神父是马相 伯在上海徐汇公学学习拉丁文的老师,1909 年的这版拉丁文—中文《圣谕广训衍》出版时,已经 去世。从笔者所见的 1909 年版来看,此第一卷的序言仍乃全套五卷本的总序言,指出了将《圣谕 广训衍》作为初级班学习材料的必要性,出版年份却晚于后四卷。因而,这很可能是一个后来的修 订或重印本(即便封页上并没有显示),于晁德莅去世之后再次印刷,归入到这套教程中去的。如 果将此 1909 年的印本单独看作是晁德莅的一项作品,大抵是西文语种有关《圣谕广训》的最近一 次全译。 三、结 语 作为初入异文化空间的新教传教士,面对“他者”的文化根基,其早期的学习态度与相应之传 教策略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即通过爬梳美国耶鲁大学卫三畏家族档案中所藏有关清代《圣谕广训》 方言直解手抄资料,进一步探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入门材料这一 “传统”之源起。鸦片战争与条约港口开放之前,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开展不仅受到地域的限制,更 18 Angelo Zottoli, Cursus Litteratuae Sinicae, volumen primum pro infima classe: Lingua Familiaris (Chang-Hai, Tou-se-we, 1909), “prooemium”, vi-vii. 19 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载《复旦学报》2005 年第 6 期,页 112-119。 10 多面临的是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方面的不足。因此,作为主要表达介质的“文本”,不仅乃当时 “福音派”传教士所坚信的有效传播途径,其撰写过程及内蕴思想更是需要后来研究者的细问推 敲。这些西方宗教观念的笃信者与传播者,如何首先成为异文化的学习者,进而加以自我改变,逐 步成为异文化的对抗者与竞争者?早期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习得、认知态度,在这 个意义上颇值得玩味。 本文旨在对传教士档案中一手资料的整理与解读,即发掘更丰富、更深入的实证材料基础之 上,进而增进对十九世纪中西交流之历史过程的认识。以卫三畏收集的十余种有关《圣谕广训》的 方言直解资料来看,其收集过程本身体现出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地方文化细致入微的 观察。结合卫三畏的生平推断,很可能是他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于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开放不 久后精心收集的,不仅有多种吴方言及福州话的样本,亦涉及到学习过程中不同的注音、释义方 式。这种“收集”方式的整体性及多样性,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以《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 “传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据现存资料所示,自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对 《圣谕广训》相关文本的关注有着很强的延续性,的确成为一种中文学习的“传统”。然而,如何 使之成为“传统”,还需针对个别文本加以细剖。文章的后半部分即讨论传教士关注《圣谕广训》 与《广训衍》及《直解》的不同出发点。与传教士关心的其他中国文学样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帝 王向民间的宣讲材料,传教士还特别重视《圣谕广训》的社会功能。《圣谕广训衍》或《圣谕广训 直解》的文本内容的确能够给外国学生提供活生生的中国地方口语实例,然而米怜等早期来华传教 士翻译、介绍《圣谕广训》及《广训衍》,则更侧重剖析其文本的伦理内涵。正如米怜 1817 年翻 译本的序言中所示“以基督教的福音增强中国人已有的向善观念”,即成为传教士学习动机的定音 之锤。此后来华传教士有关《圣谕广训》的学习文本在取材、体例、编写方式上虽略有不同,其研 习旨意却不离其宗。因此,要了解《圣谕广训》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一以 贯之的“传统”之根源,亦需从文本的翻译思想及语境等各方面相互贯穿加以探究。 四、附 第1种 Ningpo Colloquial 录 (宁波土白,原文逐字以罗马字注音,句读乃本文撰写者添加) 這孝順个道理,是天个綱常,地个道義,人个行爲。一个人弗曉得孝順大人,也弗忖忖大人愛惜兒 子个心嗎?其在抱手个時候,肚飢兌自又弗會吃,冷兌自又弗會穿。做大人个聼其聲音看其相貌, 若是笑兌,大人就歡喜起來,若是叫兌,大人就弗爽快。會走个時候,大人步步跟着,其有病个時 候,大人日弗安夜弗眠。養其教其到拉成人長大,又替其娶一房家小,謀一行事業。百樣打算費了 11 多少心機,用了多少氣力。大人个恩惠寔在像天介大。兒子要想萬分裡頭報其一分,自然當該盡心 竭力。保重自个身體,省束自个用度,服事其要勤力,供飲其要豐富。弗要戯賭吃酒,弗要逞勇造 孽,弗要单貪銅錢銀子,弗要只顧老婆兒囡。如此做法,雖即外頭个禮節有點弗到,然而裡頭个真 心寔在有餘。推单開去,像曾夫子所話,住在屋裡弗守規矩,算弗得是孝;服事皇上無得忠心,算 弗得是孝;出任做官辦事弗敬,算弗得孝;朋友來往言而無信,算弗得是孝;出兵打仗,臨陣退縮 算弗得是孝。這些都是孝子分内个事干。講到阿爹有大兒子叫做家督,阿弟有大阿哥叫做家長,每 日進出,無論大小事干,都該請教。總是還有吃食時候必要尊其,説話裡頭必要讓其,走一步路必 要比其慢點,坐東立東必要在其下首,這些事干總是做阿弟个道理。有人比我大十年个,尚且要把 阿哥介服事,其有人比我大五年个,尚且要跟在其个後頭,何況是我个親人嗎。凡百弗孝順个人, 終弗能彀和睦兄弟,所以服事大人與服事阿哥是一樣个要緊。會做孝子,總能彀做悌弟,會做孝子 悌弟,總能彀在鄉村裡頭做一个良善百姓,在行伍中央做一个忠心勇兵。將爾等做兵丁个,做百姓 个,亦曉得做兒子當該孝順大人,做阿弟當該敬重阿哥。只怕習以爲常,弗去理會,使得違背倫常 兌。若能彀其自痛痛个悔改,存至誠个心,用完其應用个氣力,從一个念頭孝弟日積月累,至于念 念如此。弗要考究虚文,弗要忽略小事,弗要外頭个名聲,弗要人家稱讚,弗要起頭勤力後頭懶惰 ,孝弟个道理,自然做得好兌。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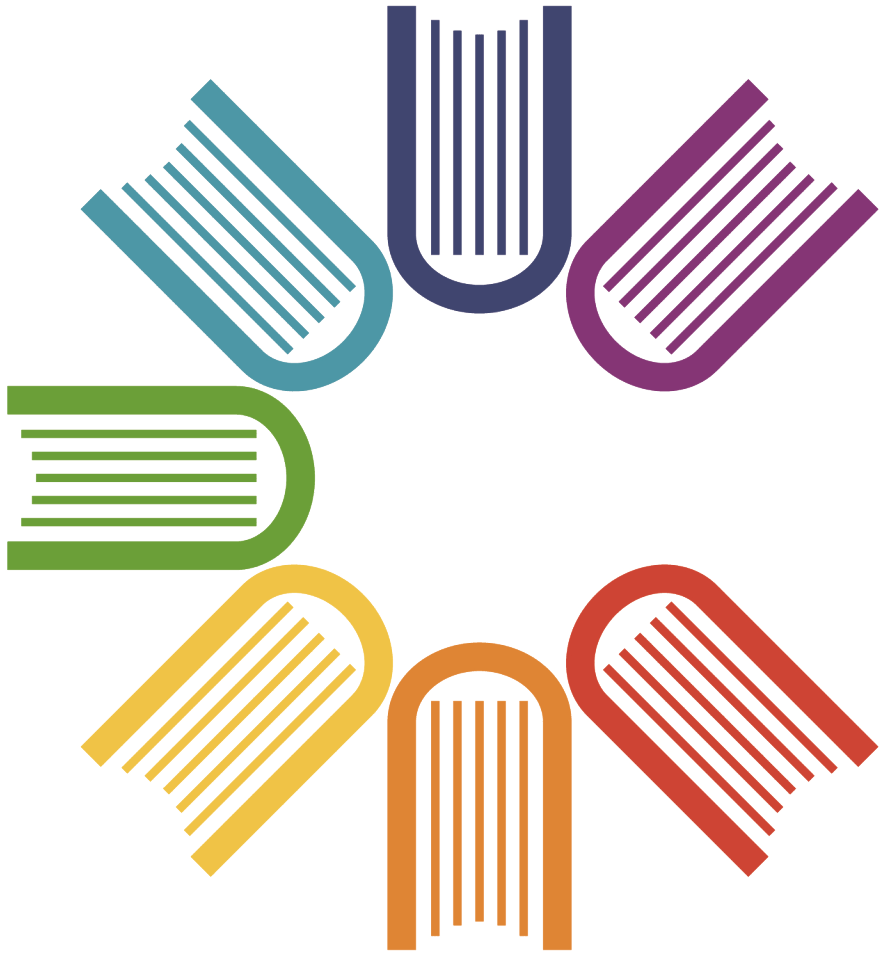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点击查看:传教士与圣谕广训.doc
点击查看:传教士与圣谕广训.doc




